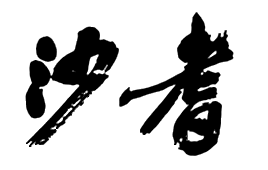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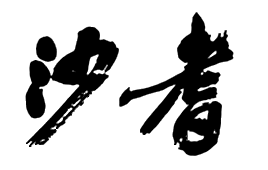

文/张端君
图/卡门艺术中心提供
如果在数年之前,问起大陆前辈艺术家"沙耆",可能很多人都不曾听闻,但随着台湾画廊业者戮力经营大陆画作,让这位被人遗忘许久的艺术家重新获得尊重与肯定。其中,卡门艺术中心虽非第一位取得沙耆作品的台湾业者,但却是最努力、最用心经营沙耆作品的画廊,经过数年的收集与整理,所累积的沙耆作品及文献资料已卓然有成。
百余件精彩作品一次呈现
今年,适逢沙耆创作达70年,为了庆祝这难得的日子,由卡门艺术中心策划,将在北京、上海及台北举办沙耆70年作品回顾展,主办单位为中国油画学会及台北历史博物馆,协办单位则有李仲生现代绘画文教基金会、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浙江省博物馆。卡门艺术中心负责人林辰阳表示,三月先在北京及上海展出104件作品;四月在台北历史博物馆二楼展览厅展出,但因为场地较小的限制,只能从中挑选80件左右作品。其中77件为卡门艺术中心用尽心血征集而来,沙耆的家属则提供4件,另外向浙江省博物馆借展20件,向中国美术馆借展3件。
展出作品在北京、上海、台北的专家经过数次筛选而出,相当精彩且具代表性,将沙耆作品做了一次最完整的呈现,从他早期留学比利时的作品到97年中风前,最后一幅创作《最后的菊花》都将参与展出。另外,写满文字、画满插图的沙耆笔记本及书籍也将一同展出,而配合此次展览更筹备了沙耆绘画艺术的座谈及研讨会,邀请两岸三地学者专家相互交流研究沙耆艺术的发现及心得。
林辰阳表示,经营大陆画家作品最初是基于商业考量,也看准未来大陆地区的收藏潜力,但是越接触大陆画家的作品,尤其是第一代的前辈艺术家,越受他们的作品所感动,况且为了画廊的永续经营,愿意花费时间、精神,甚至投入大笔经费作文献上的考证,最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好的作品不被埋没,好的艺术家能被重视及肯定,衷心希望更多人知道"沙耆",进而欣赏"沙耆",就不枉此次办展的奔波及辛苦。
被捕入狱精神大受打击
沙耆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不少大陆地区学者亦对沙耆生平及艺术做过深入的调查与研究,以下即将这些资料剪辑呈现,期望让读者对沙耆的一生及其创作有更多的认识。
1914年,沙耆出生于浙江省鄞县沙村,取名引年,字吉留。其父沙松寿为中医外科医生,历年行医、经商、执教、也擅长中国山水画。沙耆自幼体弱,生性内向,在私塾中成绩平平,却偏爱画画,自小即可看出其绘画天赋。1925年,沙耆随父亲至上海就读宁波同乡会小学,是年"五卅惨案"发生,对沙耆震动很大,在日记中他的回忆是"我虽少年不懂事,但喋血成流……,可以嗅到帝国主义的嗜血性能"。隔年,沙耆因病休学回家;1929年后经由堂兄沙孟海引荐进入上海昌明艺专就读。
1932年沙耆又转往上海美专,经常与同学参加示威游行及宣传抗日的活动;1933年6月下午,一群便衣特务及巡捕闯进沙耆住处,在床底下搜出多张共产党宣传传单,于是沙耆被捕入狱。当夜关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19岁的瘦弱青年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他是家中独子,又是两代单传,如今身陷囹圄,全家焦急万分。"每次探监,老父见到儿子,那副剃了头、穿一身蓝色囚衣的憔悴样,伤心得只能掉泪。为救儿子,父亲四处求人,花钱通关系,后来请杜月笙出面,讬病交保释放,监外就医。"
低沙耆一班的同学周闪耀回忆时表示,沙耆是曾经谈论共产主义思想,在政治方面也有一定的热情,但并没有经验,为了避免特务的搜查,当时一些革命刊物及书籍都是用《唐诗三百首》或《小学语文》来当书皮包装。沙耆被捕是因为有人密告,他父亲花了三百大洋将他救了出来,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昂贵的价格,而学费则是每月八个大洋,这也还得是有钱人家才供得起的。
因为法院尚未销案,沙耆藏匿也非长久之计,时值沙孟海任交通部秘书,建议他至南京继续求学,将其名"引年"更名为"耆",并推荐从徐悲鸿学画,接纳入中央大学艺术系为旁听生。在求学期间,沙耆对近代的东西方画风都有涉猎,渐渐显示出自己在绘画方面的天份,并以其大胆的用笔及深沉的色彩得到老师徐悲鸿的赏识。
远赴比利时在艺术创作上精进
作为一个画家的儿子,沙耆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了解,而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当别人还在用铅笔写字、画画时,沙耆已经学会使用毛笔了。由于受到家庭的影响,沙耆并没有急于在年轻一代画家中出人头地,而是后来到上海、南京看到了成名带来的益处,再加上他自己渴望在艺术上有所精进,于是,他想去欧洲,欧洲丰富的文化遗产及西方世界的绘画传统,在他看来是一个画家创新的源泉,自己应该到那儿去磨炼。 1937年,经由徐悲鸿的推荐,沙耆告别了新婚的妻子,远赴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深造。在新写实派画家巴斯天(A. Bastien)的指导下,沙耆对欧洲的传统绘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受到佛兰德斯画派及印象派的影响下,此时沙耆的作品呈现出造型坚实、笔触悦人、色彩温暖的特色,形成了静穆和单纯的格调。1939年,沙耆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此时的他完全沉浸在西方艺术的探索中,将目光转向了表现主义、野兽派、立体派等新崛起的艺术流派,创作了一系列带有东方情调的作品。
1942年,沙耆在毕底格拉第(Le Petite Galerie)美术馆举办个展,他的作品以构思简单而又独特获得四面八方的赞赏。而比利时国家历史博物馆及比利时皇后伊丽莎白也购藏了沙耆的作品,表示他们对于这位年轻东方人的肯定,因此,沙耆投入更大的热情创作了。
对于沙耆来说,大自然是一切神奇的源头,他深入大自然去了解许多前人所未尝前去的地方;花了很多时间去观察,也陷入沉思:人类在天空、海洋、河流及其它大自然事物的面前是那么渺小;花朵、树木、动物或是宗教仪式都可作为绘画的主题。
绘画已成为生命唯一寄托
1946年10月,战火纷乱、音讯阻隔,沙耆抱病乘法国邮轮回国,他满怀希望的在迎接人群中寻找自己亲人,但不知妻子早已带着儿子离开,而老父已于三年前病故,家中等待他的只有垂垂老矣的母亲。面对空荡荡的家,对妻儿的思念使他越来越焦躁,神智越来越不清楚,开始毁坏家中物品,以宣泄胸中难以排遣的压抑和痛苦,在日记中他曾写到"十多年来,危害国民一案一直未结,孟海谓之不了了之,熟知我精神上受多大的痛苦和打击……","自从离开上海看守所后,我患了精神衰弱症,常常感到有人在我后面……"。也许,沙耆的不幸被捕为他日后得病埋下精神上的种子,而家庭的离散则加剧了他的病情。
沙耆回国后,徐悲鸿聘请他为平北艺专教授,但由于精神上的疾病未能到任,后来回到故乡生活了30多年。疾病缠身虽然让生活蒙上了阴影,但沙耆并没有因此而放下画笔,他把全部的爱恨统统倾泄到画布上,他不停的画,走到哪里画到哪里,废寝忘食的画,把病中紊乱的内心波澜倾注于画布上、纸上、书页上,甚至是门上、墙上、窗上、柱子上,所有可以涂抹的地方都有沙耆画画的痕迹,在这样孤寂疾苦的状态下,沙耆仍然顽强的挣扎,没有放弃。
绘画已经成为沙耆生命唯一寄托,他对艺术如痴如醉。由于农村条件有限,没有专门的绘画工具,而沙耆带回的颜料早已用完。于是,他捡木炭笔画速写,以油漆代替油画颜料,用后山的红泥和着胶作为中国画的赭石颜料。他到村中的白墙上画,到学校的黑板上画,也到公园里画--在上海有一个留学比利时的同学会,沙耆去参加一句话也没说只顾画画,大家在复兴公园里聚会,同学会结束大家都回去了,沙耆却还在那画画。 1952年,一个欧洲艺术访问团来访,有一位艺术家向总理周恩来提到沙耆的艺术成就,但周恩来未闻其人,便转询当时的中央美院长徐悲鸿,才得知沙耆的经历及艺术造诣,知道他目前于家中养病,特派人照料并给予生活津贴。往后数年,沙耆接受了数次的精神疾病医疗,似乎有转机,但始终未能痊愈。
1967年文革期间,沙耆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家中收藏的书画被搜括一空。所幸的是,文革最初期,沙孟海以沙耆母亲名义捐了一批作品给浙江省博物馆,因而才有此次沙耆70年作品回顾展的借展。
83年举办沙耆画展获得广大回响
1981年,在距离沙村10公里的韩岭镇,有一年轻人余毅喜欢画画。知道沙村有一位奇人沙耆,他找到沙耆想拜他为师,沙耆和他一见如故于是,沙耆收了他平生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学生;下半年,在儿子沙天行的安排下,沙耆从沙村迁往韩岭镇,在这里获得较为妥善的照顾,沙耆的创作又进入了旺盛期。
余毅6月22日的日记中写到"我们每天出去走走。老师画荷花,要到西冷桥附近看荷花。前几天,画了一幅人体背部,我为模特儿,无论从素描、构图来看都很成功,非常精彩,可与比利时画的人体习作比美"。8月18日,'吃药和不吃药是有矛盾的,两者各有特点。吃药之后,人好像进入冬眠一样,糊涂的,行动不便。不吃药时,幻觉增多,但精神是好的,工作也有一定的效率,两者相比,后一种好。游泳我们已经去过,老师已经吃不消了。近来非常喜欢读书,你来时,请给他带一本屈原的离骚,他很喜欢'。
1983年由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美术学院等单位共同筹办的沙耆画展,电视台及报章杂志纷纷做了醒目的报导,获得很高的回响;北京、上海等地的艺术界人士前往参观;中国美术馆也派员观摩,并且收藏3件沙耆作品;同年沙耆画展也应邀至上海、北京展出。
画展后,学生余毅陪同沙耆到莫干山、天台山、天童寺、国清寺等风景名胜游览作画。余毅在12月29日写给沙天行的信中说"给你写回信时,窗外已是大雪纷飞,我们明天就要下山,莫干山住了已近五个月了,老师画了30几幅油画,管理处一共拿了24幅,自己留下的无非是一些人物写生和人体构图"。1989年,沙耆年事已高较少出门,手中的画笔却不曾停歇,画了大量的人物、静物和风景画。1997年3月,沙耆脑中风,由儿子接往上海住院治疗,因而放下了手中笔画。
学术界深深肯定沙耆艺术
1998年4月14日,中国油画学会和中国美术学院研究学部在北京和上海召开了"沙耆油画艺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对沙耆精湛的油画艺术无不感到震惊,他那执着艺术的精神和丰富的、饱含生命激情的艺术语言,让人发自内心钦敬,大家一致认为在20世纪中国油画史上,沙耆是一位重要人物。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卢沈:我们喜欢沙耆的画。他的意义在于他的创作心态,我们曾讨论沙耆的画为什么如此之好,我想是因为他的心地非常的纯,他忘记了一切与艺术无关的事,完全沉浸其中,是感情的自然流露。我们看了他的画之所以激动,是因为他真诚的对待艺术。他在疯了之后,丢掉了许多理性的束缚,爱怎么画就怎么画,不想别人叫好,也不想参加展览,所以他的艺术既让人亲近又让人肃然起敬,如果我们能多看一看像沙耆这样的作品,必能让心沉静下来。我最看中的就是他的创作心态,如果好好的介绍沙耆,展览他的作品,能对中国油画起很好的促进作用,使一些人清醒过来,看看到底该怎么搞艺术。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今天,我们坐下来谈沙耆的艺术,说实话,心里是很难过的。沙耆的名字,在当今的艺坛很少人知道,他被埋没了几十年,有人会说,因为他有病,所以人们对他的人和艺术淡漠了,我想,即使他没有病,有份工作,作为艺术家,他也不会受到当时社会的重视,因为他的艺术观念和实践同那时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艺术可以和政治结盟,其中不乏传技者,他们永远值得我们尊敬,然而还有另外一类艺术家,他们描写普通的事物,描绘大自然,作品没有"重大主题"。但不是没有思想,而是把思想隐藏和包含在艺术语言之中,忽视或否定这类艺术,实质也是对人性需求的一种否定。
当然我并不认为沙耆是一个彻底"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30年代国难当头,他曾提出为民族而艺术的口号,他还身体力行,于40年代创作了孙中山像,并用艺术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斗争;而中年之后他转向以画来抒发内心的情感,可以说,他是一位遵循艺术创造规律的艺术家。今天,我们重新评价这些被埋没的艺术家时,衷心希望悲剧不要重演,希望我们能从已发生的悲剧中去汲取深刻教训。
晚期创作迎来又一个高峰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徐君萱:我想提供一点关于沙耆的背景情况。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沙耆迎来了又一个创作高峰,主要的原因是他这个时期生活不错,心情舒畅。当时由沙村村支书老余(余毅的父亲)照顾他的生活,为他提供烟、酒、画布、画框、颜料,村子位于鄞县东钱湖畔,出门就有好山好水,因此沙耆画了很多风景。但他作画并不完全依照对象,比如画静物时,也摆点东西,画入许多主观色彩,表达他内心的真实。我观察过他的作画过程,看得出他对油画性能很熟悉,喜欢把调色板上剩的颜色都用掉,造成斑驳的颗粒状画面,有一种闪烁的效果,看得出他的艺术神经并未受影响,还很健全、旺盛。但作画时也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胡涂;还有些画经过反复覆盖倒显得层次深沉,油画质量高超;有时也会出现一些明显的错误,如人体比例上、景物前后关系上,这很值得研究,到底是他故意的艺术处理,还是笔误,一时还难以说清。他画画时并不像我们那么冲动,而是动作非常平缓,但内心一定有某种情绪在触发他,笔下最常出现的是异国风情、大海、白种女人、故乡山水、静物,流露出一种浓浓的怀旧感。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钟涵:沙耆艺术的光彩之所以没有被淹没而被重新发现,不是偶然的。这是开放社会各方面文化认识提高和许多人士热心支持的结果。不但他的亲属、族人,而且乡中邻里、地方文化馆到各地的美术文化机构都为他开道,作了许多事情。我直接接触到的是美术家同行们的爱护,特别是浙江画界的朋友,例如中国美术学院的画家全山石、舒传曦、胡振宇等都曾经热忱的推荐、介绍、宣扬;范景中、许江等作了精辟的理论阐发。
而台湾的卡门艺术中心特别致力收藏和出版他的作品,使之得到一个传播的条件。如果说80年代那一次的沙耆展览主要属于对他旧作的介绍,那么90年代末这一次的再发现的意义更大,因为这显示了艺术家传奇性的艺术生涯的晚期高度,一种生命悲剧后的光华,一种精神性的凯歌,沙耆无疑地会留在现代中国美术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