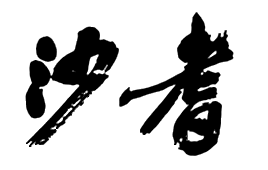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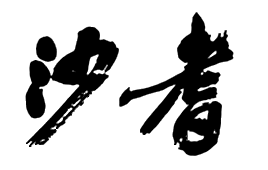

文/徐秀香
艺术新闻
2001.4
三月一日当天下午,在中国美术馆新闻发布厅召开了"沙耆艺术学术座谈会",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主持,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四十余人。 中国油画学会禹群小姐提供我们一份当天的"沙耆艺术学术座谈会"纪要,限于篇幅的关系,于此仅能节录主持人及部分学者的发言让大家先睹为快。
邵大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沙耆先生是一个边缘的艺术家,他与居于主流地位的徐悲鸿、董希文先生等有共同点,有不同点。但是他是鲜为人知的。这次展览展出他104幅作品,其中30~40年代的作品很多,这部分对我们研究中国美术史是非常珍贵的资料。从沙耆先生的作品来看,他早期的作品不论技法如何,心态是很真诚的;90年代以后的作品则是很放松、很自由,个性鲜明,完全不像一个老人,充分表现了他的才能和热情。这个展览很重要,有利于我们全面了解沙耆先生的艺术。
陶咏白(中国艺术学院研究员):沙耆是用生命走出了自己的油画艺术道路,一般来讲,中国艺术家去西方学习,根据他们对于西方油画的价值取向、切入点的不同,学习吸收和引进总是阶段性的。譬如徐悲鸿引进了比较写实的那一阶段,林风眠引进了表现主义,庞薰琹引进了现代构成主义,王悦之引进了装饰性,而沙耆则算得上一个全程式的代表人物,在封闭的状态下,走出了中国油画这样一个全程式的道路。他不去刻意追逐某一个风格、样式,而是自然而然走出来的。他后阶段的作品很难复制,无法重复,完全是一种心灵的歌唱。从他的历程看中国的油画,经过了一百年的努力,有天分的艺术家经过这样的积累,对西方的技术都掌握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放开来,达到一种随心所欲的状态,进而走向成熟。
水天中(中国艺术学院研究员):中国的画家在二十世纪后期遇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绘画的社会化、政治化与其个人创作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百分之九十的画家都遇到了这个问题、所有画家在绘画上出现的矛盾都归结到这一点上。这意味着中国画家在二十世纪后期进入到一个大批判的环境,每一个人都在想"我的画别人怎么想?","别人问我时我该怎样解释?"……在这样一种情绪下画画,无形中就有一种约束。而沙耆以他的创造和生命突破和超越了这个问题,当然他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超越,是别人不具备的环境。他以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身份获得了创作的自由。表面上,沙耆似乎也像林风眠一样对于中国的极权政治没有任何反应,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真的没有反应。从沙耆晚年的作品中提写的诗和随意写的文字里面,可以看出,他对国家的状态、人民的命运有着高度的关心,并以他特殊的紧张关注着。相比别的画家而言,沙耆算是自由的了,像他这样能够独立于自己的精神中的画家,在当今现实生活中是极少的。
郎绍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很多油画家到了一定的年龄,在技艺上就退化了,中国油画史上大器晚成的很少,而沙耆先生是个例外。由于他在国内学习9年,在欧洲学习7年,基本功相对扎实,且能进入到这种技术的娴熟运用。很多中国油画家早年出国留学,回国后心性变的淡泊,更宜心于水墨;而沙耆则不同,继承了欧洲的传统,并坚持下来。艺术过多地依赖于政治,从而导致了艺术家受多种干扰,丧失了艺术的纯粹性。而沙耆虽疯了,感情和技巧却没有受到什么损害,所以他的油画达到了一种高度,这在他那一代画家中是仅有的,甚至包括徐悲鸿、吴作人等先生都不及。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艺术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环境?
杨悦浦(中国美协编审):看了沙耆先生的原作后,有两个感触:一个就是觉得沙耆先生在运用油画语言方面,已经到了化险为夷的状态,另外就是觉得并不是说一个画家,他所有的作品都是精品,今天展出的作品也不是每件都好。总的来说,他回国以前,在比利时画的作品都非常珍贵,但不是很好;80年代以后的作品我就觉得非常宝贵,给我们留下许多让人思考的问题。我本人比较偏爱他后期的作品,这些作品中他使用了画家们都很害怕用的黑色,而他却用得驾轻就熟,不过在他使用的黑色中,能够感觉他很强烈的痛苦和忧郁。
沙天行(沙耆的儿子):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父亲的关注。在这里我提供一些关于我父亲的病理背景,也许对研究他的艺术有些帮助。我父亲的病是有遗传基因的,他小时候就有过癫痫病,后来又被关过,进一步刺激了他的病情,以至于他总是躲着别人,把自己封闭起来。据医生说,这是一种狂躁性的精神分裂症,但这种病不会24小时全天发作,也不影响感情,只是在发作时让病人逻辑混乱、颠三倒四。父亲在比利时留学时,发作过两次,住过院;回国后也有发作住院的经历。周围的人包括我在内,总是把他当成一个精神病患者,却忽视了他丰富的精神世界,导致了他的孤独,所以凭心而论,父亲一生的坎坷不在于物质上的贫乏,事实上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他的经济条件一直还算不错的,而是精神上的孤独和痛苦。根据找到的一些资料,表明他内心的矛盾与冲突是非常厉害的,主要有两方面的冲击:一方面是他对艺术的追求与维护家属亲情之间的冲突,当时他在比利时发展得非常顺利,而家里恰巧在那时候急迫地催促他回国,他无法放弃比利时的艺术创作事业,却又要忍受内心感情的折磨;另一方面是他自己的艺术主张与恩师徐悲鸿所希望的方向之间的冲突,以至于他总感觉对不起徐先生。这些冲突对他的病情刺激很大。而且他回国后居住在农村,与农民之间无法交流,内心是非常郁闷和孤独的……我作为他的儿子却不能够了解他,感到很对不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