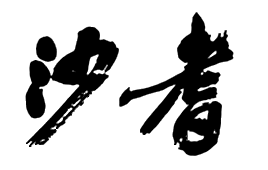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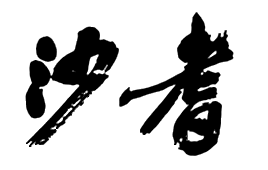

范景中
新美术
1998.4
艺术是一种不可言喻的东西,它们的创作者则充满了传奇的色彩:他们有非凡的才华,却受到压抑;他们有神性的创世才能,却受到贫穷与孤独的磨砺;他们生不逢时,死后却荣誉纷至,辉耀青史。这种观念经过了浪漫主义的渲染,已经成了撰写艺术家传记的常用模式。
我们正在讨论的艺术家沙耆,也带有几分这样的色彩。然而,却无须我们的渲染,因为他本人就生活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可以和他交流,向他提问,面对面地了解我们感兴趣的一切东西。但遗憾的是,贫穷、孤独,与长期徘徊在精神世界的阴影,已扰乱甚至摧垮了他的理智。只有艺术的感受,艺术的才能,艺术的创造力,才能不受种种厄运的束缚,不时地像长河巨浪般地汹涌而出,把他的感受、他的追求、他的痛苦与他的心灵之光倾泻在他的画幅上。
他虽然活着,但我们和他之间却飘浮着一种谜样的气氛。我们不了解他的性格和气质,不了解他创作的动机和思绪,甚至对他的历史也所知甚微。他早年在上海美专和中央大学学画的经历,嗣后赴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深造的经历,二战期间和毕加索等人一起办画展的经
历,这些昔日的光辉,连同他的"为民族而艺术"的豪言壮语,都已渐渐地消失在历史帷幕的背后,我们所能寻回的只是一些零星的信息而已。 然而,凡是观看过他的作品的人,几乎都受到了强烈的震动,甚至骤然产生了一种感觉:它们应当归入中国最伟大的油画之列。这种感觉是否真实,平静之后,我们已在思索,而实际上我们越思索就越加坚定了这样一种信念:应该把这位艺术家写入历史,而不是仅仅报道他的新闻。
在我们一瞥沙耆的艺术之前,先环顾一下艺术家的画室也许是有益的:这是一座破旧的房屋,角落里放着一张普普通通的木床,旁边堆叠着一些破旧的画箱;屋子中间没有隔板,甚至连家俱也难得一见。可以说,它已经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这就是艺术家起居和绘画的地方。然而,这座简陋的房屋却像他的伟大同行的画室一样,也蕴含着创作的灵感和工作的尊严,因为艺术家已然把它变成了一部巨大的作品,一部异乎寻常的作品。他就像虔诚的画工画洞窟,就像伟大的艺匠画教堂那样画他的房屋。它的中间虽然空荡、冷清,但是四面的墙上和柱上却布满了眩人眼目、震人心魄的形象。这是一些粗犷有力的人体,这就是沙耆每天不停地所画的作品。他一遍又一遍地勾画,没有了空隙就在画上作画……他就这样默默地工作了三十个春秋。
然而,这是怎样的一种默默的工作啊,他几乎总是处于那样一种创作的狂热之中,他不仅画他喜爱的人体,画他喜爱的简单、平凡、日常所见的景象,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也要唤起色彩本身的威力,来表达他内心的难以遏制的冲动。甚至,为了这种冲动,他不惜抛弃他往昔苦心孤诣所学来的素描技巧和构图规则。我们知道,正是那些技艺,为他早年在欧洲赢来了无尚的荣耀,成了他跻身于伟大艺术家行列的凭证。而现在他要让色彩的光芒照亮他的世界,也许只有在那里,他才会欣然地凝视他所赞美的景象:
我全神贯注地看着比亚特丽斯,但她光彩璀璨,以致使我感到神迷目眩。--神曲·天堂篇,Ⅲ ,127-9
正是在对色彩表现力的探索上,他和中国的传统绘画背道而驰。按照传统的画法,艺术家画秋天的丛林,就不该描摹树叶的绚烂色泽,而应该写出那无形的秋思或秋意。而沙耆所看重的恰恰就是这色彩绚烂的有分量感的东西。尽管沙耆不是一个狭隘的色彩主义者,尽管他往往缺乏他所想用的那些颜料,但是在画出色彩的震撼力上,没有几个中国的油画家能和他相比。不过他却从来不摆出创新者的姿态,更不想引起新闻界的注意,事实上,他几乎已不再指望人们看他的画了,就像塞尚和凡·高一样,他要画下去只是因为他不能不画。但是,我们却不能不就此停笔。这篇短文意在勾出一幅沙耆的印象式速写,要想深入地了解他的精神世界,最好是去看他的作品--那是由一系列杰作构成的艺术家的思想传记。